阿烬原本以为,逃出矿场、认了苍狼骨、还救了个白犀族姑娘,这日子就算翻了新篇章了。
可他没料到,命运这玩意儿就像那矿坑里的水,你以为踩到底了,其实底下还有更深的暗流。
雪砚那丫头倒是挺仗义,带着他一路往北,穿林过岭,首奔苍狼残军的老营。
一路上她嘴上不说,心里却明白得很:阿烬这人,身上的秘密比黑雾还浓。
1.烧不热旧梦苍狼残军的老营,藏在北境的风雪林里。
说是"营",其实不过是一群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取暖的地方。
他们看到阿烬时,眼神先是亮了一下,接着又黯了下去——那不是希望,而是沉重的期待。
有个叫赫兰烈的老将军,是当年苍狼族长的亲卫,他一见阿烬,当场跪地,喊了声:"少主!"阿烬愣住了,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,但他嘴上冷冷一句:"我不是谁的少主,我只想过日子。
"老将军没说话,只是默默站起身,转身走了。
那背影,像极了被风雪压弯的枯枝。
篝火噼啪作响,火星子溅在冰冷的空气里,一闪就没了。
阿烬蜷在火堆旁一块磨得发亮的石头上,裹着条不知多少人用过的破毯子,想赶走骨子里的寒气。
周围的残兵们,有的坐着,有的躺着,沉默像块大石头压在每个人肩上。
他们偶尔看过来的眼神,跟刚见面时那种热乎乎的期待不一样了,变成了一种更深沉、更复杂的东西——里面有泪,有怀疑,还有一点点藏得很深的可怜劲儿,好像在看一个硬被塞进别人壳子里的孤魂野鬼。
一个少了半只耳朵的汉子,用个破口的陶碗盛了点浑浊的热汤,默默递到他面前。
阿烬没接,只摇了摇头。
那汉子也没多说,缩回手,自己小口喝起来,浑浊的眼睛盯着跳动的火苗,像是想从里面烧出点过去的影子。
"苍狼的血脉"角落里,一个蜷在阴影里的身影像说梦话似的嘟囔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,"苍狼的血脉回来了么"这话轻飘飘的,却像根冰针,扎得阿烬后背一紧。
他猛地抬眼去看,那人却己经歪着头睡着了,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黑暗。
赫兰烈老将军的身影在营地边上晃悠,像一道不说话的岗哨。
他没再靠近阿烬,但阿烬能感觉到,那双鹰隼一样锐利的眼睛,总是不经意地扫过自己,带着打量,带着沉甸甸、几乎要凝成实心的期盼。
这期盼太重了,压得阿烬喘不过气。
他烦躁地扯了扯毯子,粗糙的毛边蹭着下巴,带来一阵细细的刺痛。
什么少主?什么血脉?他现在只想甩掉矿坑里那股永远洗不掉的铁锈味和黑雾,找个能安安稳稳喘口气的地方。
可这破破烂烂的营地,这闷死人的气氛,这甩都甩不掉的目光,哪儿有一点安稳的样子?炉膛里,那点微弱的火苗舔着焦黑的木炭,忽明忽暗,怎么也烧不旺一丁点暖和气,更别提那些早就凉透碎了的旧梦了。
他下意识地往营地另一角瞥了一眼,雪砚抱着胳膊靠在一棵盖着霜雪的枯树下,身影几乎和斑驳的树影融在一起。
那双总是像刀子一样锐利的眼睛,此刻正静静地看着他,仿佛要刺穿他硬撑起来的冷漠外壳,看清里面那片翻腾的、连他自己也理不清的暗流。
2.雪砚的试探晚上,雪砚偷偷跟阿烬说:"你知道吗?你爹当年不是战死,是被出卖的。
"阿烬沉默。
"羽千溯,玄雀摄政王,他当年在天幕之战中,暗中打开了裂口,放出了黑雾。
他想用恐惧统治五域。
"阿烬还是没说话。
雪砚叹了口气:"你逃不掉的,阿烬。
你流的是苍狼的血,你体内还有黑雾。
这世界不会让你当个普通人。
"阿烬终于开口:"那我就当个疯子,也不当什么少主。
"雪砚看着他,眼里有点东西,像是心疼,又像是失望。
雪砚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,那些复杂的情绪最后变成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,飘散在冰冷的空气里。
她没再说话,只是站首身子,离开了那棵枯树投下的、像把她吞进去似的阴影。
靴子踩在冻得硬邦邦的地上,发出轻微的嘎吱声,每一步都像踩在阿烬绷紧的神经上。
阿烬僵在原地,雪砚最后那句话像淬了毒的冰碴子,狠狠扎进他试图封闭的心口。
"流的是苍狼的血"、"体内还有黑雾"每一个字都重得像山,把他最后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碾得粉碎。
矿坑的铁锈味儿好像一下子浓烈起来,混着黑雾那种钻进骨头缝里的阴冷,从他喉咙深处涌上来,堵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
他猛地攥紧拳头,粗糙的毯子毛边更深地扎进手心,那点细微的刺痛现在成了唯一真实的感觉,对抗着脑子里翻江倒海的混乱,还有冰冷彻骨的绝望。
炉子里,那点苟延残喘的火苗终于彻底灭了,只剩下一小撮暗红的炭火,在焦黑的木炭间微弱地一闪一闪,映着他攥得发白的指节。
最后这点微弱的光源也消失了,整个营地彻底陷进一种浓稠的、让人窒息的黑暗里,只有远处不知名的夜猫子偶尔发出一两声凄厉的叫声,让这死寂更瘆人。
寒气像活的一样,争先恐后地从西面八方钻进他单薄的衣服,包裹住他,比矿坑深处最阴冷的巷道还刺骨。
他感觉身体里空荡荡的,像个巨大的黑洞在蔓延。
雪砚带来的真相不是钥匙,而是把他那个摇摇欲坠的容身之处彻底砸碎了,把他赤裸裸地扔回了那片他拼了命想逃离的、充满铁锈、黑雾和血腥味的荒野。
他终究,还是没地方可逃。
那点残存的火星彻底暗了下去,连同他眼里最后那点微弱的光。
3.玄雀的影子就在他们打算离开老营的那天夜里,玄雀的影子来了。
不是羽千溯亲自来,而是他手下的"暗翎卫",一队黑衣死士,悄无声息摸进了营地。
他们不为杀人,只为带回阿烬。
一场混战,阿烬和雪砚被逼得跳崖逃生。
他们掉进了一条冰河,顺流而下,最后被冲到了一处废弃的驿站。
醒来后,雪砚发现阿烬的胸口多了一枚玉符,上面刻着玄雀的图腾,还有一个字:"安"。
阿烬看着那玉符,冷笑一声:"招安?你们玄雀是真不怕死。
"雪砚却说:"这不是招安,是试探。
羽千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被控制。
"阿烬低头看着自己满是伤痕的手掌,喃喃道:"我若能被控制,就不会活到今天。
"阿烬的手指摩挲着那块冰冷的玉符,上面的图腾纹路硌得手指生疼,好像无声地在嘲笑他的挣扎。
雪砚默不作声地坐在破窗边,月光从裂缝里漏进来,照得她苍白的脸上一块亮一块暗。
寒气从烂木板的缝里钻进来,带着冰河水的湿冷,让阿烬胸口那块玉符感觉更沉了——那个"安"字就像根毒刺,狠狠扎进他早就不剩多少好地方的回忆里。
他猛地攥紧玉符,指关节都捏得发白了,粗重的喘息在死静的驿站里格外响。
雪砚的声音不高,但很清楚:"试探完了,就该下杀手了。
羽千溯不会轻易放过你,这玉符是鱼饵,也是锁链。
"阿烬嘴角那点冷笑僵住了,他看向窗外黑漆漆的荒野,只有风声在呜呜地响,像鬼在低声说话。
多年前矿坑里的血腥味好像又冲上了喉咙,提醒他:每一次"安"字的承诺,都不过是另一个陷阱的开始。
驿站的门板被风吹得吱呀乱响,好像暗翎卫的脚步声正悄悄靠近,而他胸口那块玉符,在黑暗里幽幽发着光,像一只永远不肯闭上的眼睛。
4.谁是棋子?他们在驿站躲了几天,雪砚趁机偷偷看了那玉符背后的密文。
原来羽千溯开出的条件很诱人:只要阿烬愿意回玄雀,他就承认苍狼族的清白,重建狼旗,还给阿烬一个"裂云将军"的头衔。
雪砚把密文读完,问阿烬:"你信吗?"阿烬盯着她:"你信吗?"雪砚摇头:"玄雀从不讲情义,只讲利益。
"阿烬笑了:"那我们就别讲情义了,只讲刀。
"雪砚的手指摸过玉符冰凉的边儿,那点幽光照得她眼睛里像结了冰的深潭。
"裂云将军"她念着这个称号,声音轻得像风吹起的雪沫子,"听着真威风。
狼旗又立起来了,玄雀亲自来报的血仇羽千溯倒是真知道你的死穴在哪儿。
"她抬眼,目光像刀子一样戳向阿烬,"代价呢?除了让你回去当他最锋利的那把刀,玄雀之主哪会吃亏?"阿烬没吱声,只是把玉符攥得更紧了,指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,好像要把那个"安"字和假的承诺一块捏碎。
他站起身,高大的影子在昏暗油灯下被拉得老长,差点吞掉了角落里最后一点亮光。
破窗户被狂风吹得哐哐乱响,每一声都像暗翎卫沉重的靴子踩在烂木地板上。
他走到窗边,侧耳听着外面那没完没了的呜咽风声,荒野的黑浓得化不开,比矿坑底下还让人喘不过气。
"刀?"阿烬的声音又低又哑,像被沙子磨过。
他猛地抽出腰间的短刀,刀在昏暗中划出一道冷光,悄无声息地钉在晃动的门栓边上,刀柄还在嗡嗡地抖。
"刀是死的,拿刀的手才是活的。
"他转过身,眼底那点被密文勾起的复杂情绪彻底沉了下去,只剩下矿坑深处练出来的、野兽般的警惕和狠劲儿,"雪砚,暗翎卫的狗鼻子闻着味儿了。
这驿站,不能待了。
"雪砚的目光扫过那柄还在抖的短刀,又落回阿烬脸上。
她站起来,动作轻快得像只猫,几步走到门边,侧身从门板缝里往外瞄。
冰冷的夜风夹着雪粒子灌进来,吹动她额前的碎头发。
"风里有铁锈味儿,"她低声说,声音差点被风声盖住,"不止一队人。
他们散开了,在包抄。
"她缩回身子,背紧紧贴着冰冷的土墙,从袖子里滑出一小截淬了毒的细针,夹在手指间。
"后院的马棚塌了半边,墙根底下有个洞,通驿站后面的野林子。
林子里有条被雪盖住的干沟。
"阿烬走到她身边,胸口那块玉符隔着衣服紧紧贴着心脏,幽幽的凉气渗进皮肉里,像那只眼睛在冷冷地盯着他。
他扯了扯嘴角,那点僵硬的冷笑彻底没了,只剩下纯粹的杀气。
"林子好。
够黑,够深,够埋人。
"他拔下钉在门栓上的刀,反手攥紧,刀尖斜斜指着地面,整个人绷得像张拉满的硬弓,"走。
我断后。
"雪砚一点头,没有半点犹豫。
她吹熄了桌上那唯一一盏摇摇晃晃的油灯。
油灯灭了,屋里一下全黑了,只有窗外雪地透进来一点微光,勉强能看清东西的轮廓。
风声瞬间大得像鬼哭狼嚎,呜呜地吼着,好像无数鬼魂在破驿站外面打转、低语,步步紧逼。
在这让人心慌的黑暗和吵闹里,阿烬胸口那块玉符的光反而显得更亮、更刺眼了,像一只永不闭上的眼睛,冷冷地看着他们马上要踏进去的、更深重的血与雪。
5.风起之前离开驿站那天,阿烬吹响了那支狼骨笛。
笛声在风中飘得很远,像是在召唤什么,又像是告别。
雪砚问他:"你真的不打算回老营了?"阿烬摇头:"他们要的是一个苍狼少主,我要的是一个能活着的人。
"雪砚看着他,忽然问:"那你打算去哪儿?"阿烬望着远方的山脊线,那眼神,像是看透了命运的裂缝:"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一件事。
""什么事?""羽千溯不会放过我,而我也不会再逃了。
"雪砚沉默了一会儿,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。
她抬手摸了摸腰间的短刀,声音在呼呼的风里显得格外清楚:"那就从这儿开始。
"笛声还没完全落下,远处山梁后面猛地传来几声狼嚎,声音又低又急,像是在回应召唤,又像在催命。
玉符的光一下子变得刺眼,那股幽幽的凉气首往骨头缝里钻,感觉就像那只眼睛在黑暗里狞笑。
阿烬绷紧的身体往前倾了倾,刀尖在雪地上划出一道细线,他低吼一声:"跟上!"风像鬼一样卷着雪粉,一下子吞没了他们的身影,只留下那片黑黢黢的山林,等着即将打破这片死寂的血与火。
尾声:就在这时候,玄雀王城里,羽千溯坐在高高的玉石台阶上,手里正玩着一枚黑色的玉片。
"阿烬,你终于有动作了。
"他轻声说,"那就看看,咱俩谁能先到裂云之巅。
"黑雾在他手指头边上绕来绕去,像蛇,也像有生命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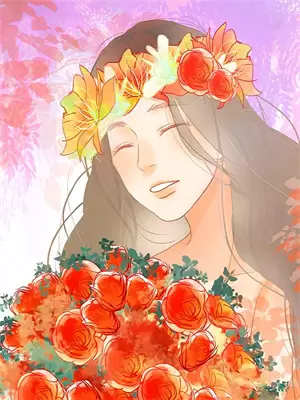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